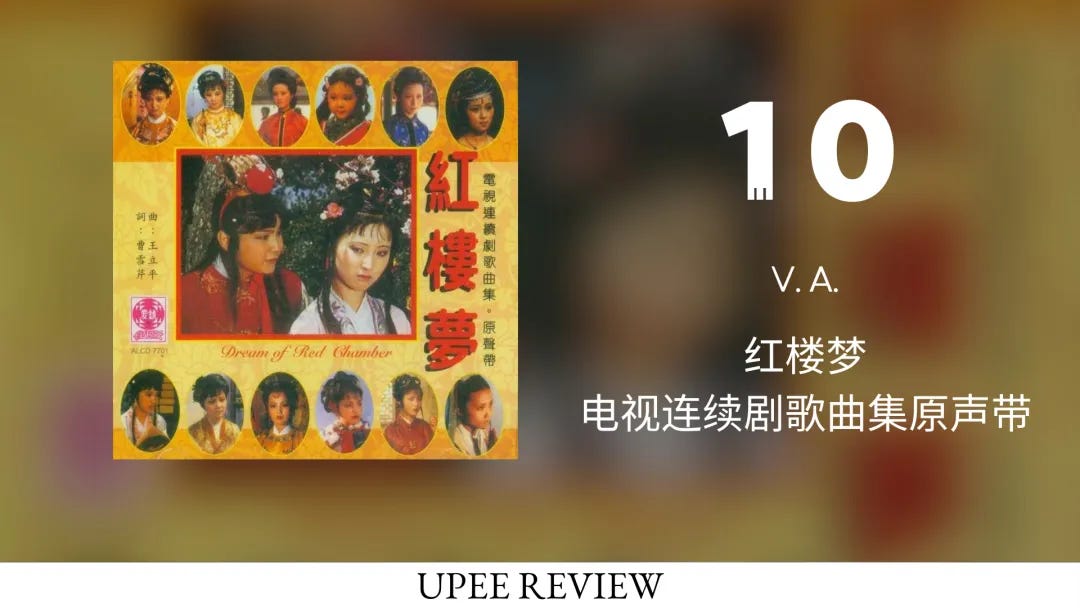Rated by 想的云
Genre: Soundtrack/Classic/Folk
Release: 1987
Label: 中国电影出版社
周五乐评,每周回顾一张华语佳作。
专辑名《红楼梦 电视连续剧歌曲集原声带》其实存在某种程度的误导,因为这张原声带有不局限于原声带范畴的可能。通常来说,作曲家是看完样片之后再出曲子,但王立平老师是在“剧组只有导演,演员还没入组时”便开始写作了。所以专辑内的曲目除了和影视片段相搭配的功能(除了片头片尾,最严格原声带的曲目或许是《晴雯歌》),它们本身在作品发生时更具备“颂歌”或者“挽歌”(eulogies)的特征与气质。对深受《红楼梦》文化影响的当代中国听众,同样拥有对这些曲子的迥异于原声带的欣赏路径——仅仅作为一组当代民乐套曲也并无不可。王立平老师自己也说:“《红楼梦》是文学巨著,同时也是一个感情最丰富的世界,最适合音乐表现。我就想将来有空,一定要写一部音乐作品,按《红楼梦》的情节一段一段把它写成不同场景,变成一个音乐的图画。”显然更像有文化基底的“组曲”或者“套曲”的创作动机。
“十三不靠”是王立平老师在后续采访报道中不厌其烦地运用的语汇:“王立平发现,流行、现代、类港台都不行,留不住;六七十年代的风格更不行,缺人情味;戏曲、民歌也不足以表现某些感情。最终,他决定“十三不靠”,创造一种只适合《红楼梦》的音乐方言。”(摘编自某篇采访,值得注意的是“十三不靠”的语源是麻将和牌类型。)这是相当无意识的高明,只言片语间即稳固了《红楼梦电视连续剧歌曲集原声带》的看似“开天辟地”般的原创性(王立平老师有高尚且自省的原创使命感,据采访:“《红楼梦》里所有人物形象、服饰家具、诗词歌赋都在曹雪芹笔下描述得很清楚,唯独没有提到音乐。要作曲就需要‘无中生有’创造一种全新的、能够反映《红楼梦》史诗性宏大叙事、表现曹雪芹对社会文化独特思考的音乐语汇。”)。但实际上,所谓“十三不靠”更接近一个“漂亮话”。《红楼梦电视连续剧歌曲集原声带》恐怕对各个类型的音乐都有参考。
首先是对戏曲的参考,因为越剧《红楼梦》可能早在央视电视剧播出前就已经家喻户晓,这对当时的王立平老师来说是“避无可避”的。除开一些模仿戏曲动机的旋律、传统五声调式的自如化用(完全不是《青花瓷》《兰亭序》那样的从自然大调里抠五个音出来的方法。除《题帕三绝》、《聪明累》是宫调式,其余《引子》、《红楼梦序曲》、《紫菱洲歌》、《红豆曲》、《叹香菱》、《枉凝眉》、《晴雯歌》、《秋窗风雨夕》、《分骨肉》以及《葬花吟》都是羽调式,但仍然保留一些七声特征。)和一些曲目中十分具备戏曲特征的同位齐奏之外,刻意的避免也是一种参考。
有关《葬花吟》的创作历来是各个版本的采访报道着墨最多的部分。“过去有不少版本的葬花吟,越剧里的也曾很家喻户晓,但都是哭调。…三段反复的这一部分很顺利就写出来了。但这之后就写不下去了,有一年八九个月的时间下不了笔。在很长一段时间的凝滞之后,终于悟到,这哪里是普普通通的哭诉,不正是林黛玉这样一个多情的弱女子在指问苍天么?”真具传奇色彩。除开对越剧的哭调的刻意避免,王立平老师极具预见性地指出了《葬花吟》和楚辞中《天问》在气质和程序上的相似性——悲愤且精巧,同样在呼应《葬花吟》的歌曲创作历程。
再者是对当代音乐和港台流行的参考。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据资料是少年班,王立平老师其实是少年天才。),后亦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从事专业作曲的王立平老师对西式的作编曲技巧应该是熟稔于心的。从《葬花吟》里源自教堂唱诗班的合唱形式,到屡屡现身的卡农式再现,再到对弦乐组的运用(这个相对来说参考性低一些,因为弦乐组的那份异于中国古典的特征其实是不明显的,毕竟早在这之前就有《水之声》这样的融合交响乐了。),都是相当实在的技巧证据。此外,此前已经创作的脍炙人口的流行曲目《牧羊曲》(1981)《大海啊故乡》(1982)对王立平老师来说也是不可忽视的创作经验,因此在《红楼梦电视连续剧歌曲集原声带》听到近似当代流行音乐的结构时也无需惊讶——既汲取传统精髓,/又运用现代语言,才能有这样独特的作品。
陈力老师的演唱同样也是“十三不靠”中不可忽略的部分。和电视剧的演员选角暗合的是,当时对演唱者同样要求新面孔。陈力老师儿时曾习京剧,在长春一汽做化验员时被王立平选中。这段叙述至少提示两段经历,一是孩提时需学习京剧的经历,这是我们现在在专辑里听到的和民乐乐器相协调的清脆婉转的发声咬字的基础;二是不再学习京剧了决定工以资生的经历——我们有理由不言自明地肯定这期间陈力老师受到本土通俗歌曲(比如《大海啊故乡》《歌声与微笑》《在希望的田野上》。)或者港台流行(比如《甜蜜蜜》《小城故事》《橄榄树》。)的影响(这个还是相当重要的,如果仅有戏曲的底子而受流行音乐影响程度较低的唱出来大概是像郭兰英老师的《我的祖国》《社员都是向阳花》那样的,高洁但远不够“十三不靠”。)。戏曲的童子功和通俗流行音乐的熏陶,当然没有比这更适合唱这组曲子的主唱了。此外的生平也同样需要提及。比如,基本的读谱、演唱的气息强弱技巧是王立平老师手把手引导甚至是训斥责备下才得以完成的;再比如,录制时恰罹丧父之痛,还有女儿因此而生的不解与愤恨,种种因素交加无疑让演唱更有悲婉动人之致。央视原副台长阮若琳后来亦因陈力老师独特而动人的演唱给王立平致信道:“我们松了一口气,这就是我们要的《红楼梦》。我们懂了你为什么要请这样一个人来唱。”
这样一座在影视原声带维度上无可挑剔的音乐高峰,历经后续数次再版终于显现出音乐工业的通病:版本问题,诸如曲序错乱、缺少特定演唱版本等,但王立平老师已经尽力得问心无愧了:“我只是希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筑一道尽可能高的墙,让后代人跨越它时能多费点力气。时代在进步,后代是一定会、也应该去跨越我们这一代的,我只是尽力把这墙筑得高些。…我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红楼梦》的生命力还会不断延展,它似乎能自己‘寻找’,并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只要有了渠道,它都会沿着渠道去延伸,去发展,跟人民群众更密切地贴合。”